 第十放映室2019-08-23 19:58:37
第十放映室2019-08-23 19:58:37
今天我們來聊聊最近大熱的《寄生蟲》。
首先,這部電影獲得了72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大獎,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獲獎。這還不算,你看看競爭對手的名單,簡直是神仙打架,大師俯拾皆是:佩德羅·阿莫多瓦、肯·洛奇、吉姆·賈木許、昆汀·塔倫迪諾、達內兄弟、泰倫斯·馬力克……能在這份名單裡脫穎而出,而且還是全票當選,《寄生蟲》的生猛可想而知。在韓國本土的觀影人次已破千萬,連續數日穩坐票房冠軍。影片的海外版權也已銷售至192個國家,超過此前《小姐》保持的176國記錄。自8月6日出資源到目前,已有20萬+人標記看過,評分雖有小幅回落,但仍然高達8.9。印象中,影史上的金棕櫚獲獎影片能拿到這樣高分的,屈指可數。
看完後,不禁想起魯迅先生的那句話:“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,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。”影片中的金家四口,生活在底層。他們住半地下室,一家人都沒工作。背後的用意極其明顯,奉俊昊想拍的不止是貧富兩個家庭,而是貧富兩個階層。那是一條長長的路,需要不斷向上走,越走,路會越寬越亮,直到通往富人家的庭院。這個鏡頭告訴我們,貧富之間的差距何其巨大,而窮人的上升又何等艱難。藉著基宇成功進入樸家,金家的其餘三口相繼混了進去。父親金基澤當起了司機,母親忠淑做起了保姆,女兒基婷做了心理輔導老師……不知不覺,窮人一家全面接管了富人家的生活。這整個過程裡,樸家人像是白痴一樣,目送著金家人一個個混入上層。但你一定也感覺到了,表面的歡喜之下,必然危機四伏。就在金家人沾沾自喜之時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,將整個局面推向失控。他們其實精明得很,精明到懂得把“精明”用在刀刃上。至於僱傭人這等小事,又花不了幾個錢,當然不值得他們費心。金家人本以為揩了富人的油,正滿心歡喜,但實際上他們剝奪的,只是另一幫窮人的生存機會。這整個故事,哪是什麼鳩佔鵲巢,到頭來,不過是底層人狗咬狗的慘劇。他們只是扔了一把狗糧,至於是哪隻狗吃了,他們根本不關心。奉俊昊最高明的地方,就是沒有把片中的富人刻畫成壞人。如果他不是富二代的話,那麼某種程度上,他還成了窮人的榜樣。在階級固化如此嚴重的社會裡,他自狹路衝出,爬上人生巔峰。可與此同時,一旦他完成了階級躍升,成為富人,也就意味著和原來的階級徹底告別。就像片中所說:“我要是成了富人,我比他們還善良。”同樣的,這句話中的“善良”,還可以置換成任何一個詞,比如:慷慨、樂觀、冷漠、高傲……只要有了錢,你就擁有了某種“任性”的權力,這是隱藏在貧富差距背後,那個更大的差距。正是這個差距,決定了富人與窮人之間根本無法和諧相處。但他們所處的位置,對於窮人而言,已是一種天然的威脅。不是我主動要傷害你,只是階層的落差,勢必會對弱者不利。在這一點上,阿方索·卡隆的影片《羅馬》有過極為精準的展現。影片中的主僕二人同時處於巨大的傷痛之中,但面對悲傷,主人可以肆意哭喊、遷怒,僕人卻只能沉默吞聲。到了《寄生蟲》中,我們看到這種“無意傷害”,幾乎無處不在。說白了就是,你給我打工,就做分內的事,但凡涉及一丁點私人感情,都是僭越。具體到影片中,前後兩次,當金司機向樸社長說起“您真的很愛太太”時,樸社長都露出鄙夷的神情,彷彿在說:就你,也配和我聊感情?暴雨過後,金家被雨水淹沒,一家人只能在體育場過夜。結果轉過天來,樸家辦起了聚會。那時樸太太說了一句話,驚心動魄:“都賴昨天的雨,毀了我們的露營,但也因禍得福,有了今天的聚會。”你可以想象嗎?那時在一旁聽著的金司機,是何等感受?同樣一場雨,對他來說是家破人散,對富人來說,卻是聚會的由頭。那味道,甚至連尚未建立階級觀念的孩子也能聞出,他說:“他們身上都有一股味道。”是窮人味,它擴散到空氣裡,象徵一種無形卻永存的歧視。那歧視,一次又一次猛擊在金司機的心上,直到將他徹底壓垮,於是他舉起刀,刺向了樸社長。富人不壞,卻依然給窮人造成了傷害,這才是階級對立中最最殘忍的事兒。
它並沒有把責任一味推給社會、富人,相反,它也讓我們看到了窮人的不堪。影片開始時,敏赫給金家帶去了一塊寓意著好運或希望的石雕。這句話把一個底層人的心思寫活了,比起虛無縹緲,不如此刻吃飽。當金司機突然感慨:“不知那個被辭退的司機,找到工作了沒有。”女兒基婷突然發飆,大喊:“管好自己就好了,管別人幹嘛?”那一刻,奉俊昊“不懷好意”地安排窗外響起一聲炸雷,彷彿這是一句會遭天譴的話。結果最終,那個被金家搶了飯碗的人,舉刀殺死的第一人正是基婷。其實覆盤整個故事,你會發現,但凡窮人之間有一點點“互利”的意識,結局也不會如此悲慘。趁樸家外出露營,金家四口坐在豪宅的客廳裡,吃吃喝喝,享受著主人般的虛榮,全然不知災難將至。這種“不思進取”的另一面,還體現為一副“小人得志”的嘴臉。沒錢時,醉酒的鄰居在門口撒泡尿,一家人不敢管;稍微有點錢了,金家父子立馬來了精神,衝出門去驅趕。有趣的是,金家最終是被大雨吞沒的。彷彿在說:鄰居的尿,你趕得走,可老天爺的尿,你還躲得了嗎?金家故意不關窗戶,只為了“蹭”外面噴進來的殺蟲藥。把兩處結合在一起看,格外有趣,就像在說:那場大雨是對於“蹭”這種行為的懲罰。還有父親說的,“不要有計劃,因為沒計劃就不會犯錯。甚至連殺人,也不算錯。”如果金家的整個遭遇,還有一點點意義的話,那就是讓兒子基宇意識到了“計劃”的重要,這是擺脫貧窮的第一步。於是在影片最後,他寫下了自己的計劃:他想要成為富人,想讓家人重新回到陽光下。儘管那是一個夢,但有了計劃,人終歸離夢更近了一步。
要說奉俊昊,有兩個關鍵詞不得不提:第一是“社會派”,第二是“反型別”。其實也很好理解,奉俊昊是社會學出身,這是他的底層思維。不信你看奉俊昊的前作,幾乎都可以當作“社會學論文”來看。《殺人回憶》探討的是:一個變態的社會是如何殺人於無形的?《漢江怪物》探討的是:一個無能的政府是如何毀掉普通人的生活的?《母親》探討的是:對弱者的同情會通向必然的正義嗎?《雪國列車》探討的是:如何推翻一箇舊世界,建立新世界?它探討的是:一個貧富差距巨大又缺乏流動性的社會是什麼樣的?為此,奉俊昊以樸家、金家、老保姆一家為代表,搭建起一個社會模型。在這個社會模型裡,除了高高在上的富人(樸家)外,只剩下兩類窮人,一類為富人打工(金家),一類靠富人養活(老保姆的丈夫)。但問題是,這一次奉俊昊太追求社會模型本身的嚴謹性了,以至於造成兩個弊端:因為奉俊昊太清楚自己要什麼了,把房間結構蓋得太死,也就少了靈動的餘地。兩部電影都在探討社會問題,但很顯然,《殺人回憶》的餘味是更濃的,它更像是自然生長出來的,而《寄生蟲》明顯是造出來的。
奉俊昊拍型別片,卻從來不拘泥於型別框架,相反,他還總想著有所突破。而犯罪片所宣揚的主流價值是“正義必定戰勝邪惡”,可看過《殺人回憶》的朋友都知道,這部電影最後也沒有抓到真凶。儘管影片緝凶的過程很精彩,可片中的警察卻一次次錯認凶手,故事也一步步滑向灰色的結局。這才是奉俊昊電影的魅力所在,他總能在滿足一種型別期待的同時,適當顛覆一下主流價值,給觀者留下反思的空間。比如長片處女作《綁架門口狗》,講一個失意的中年人被門口的狗叫聲吵得心煩,於是想殺死那條狗。但你覆盤整部電影,會發現,究竟是什麼換來了生活秩序的恢復呢?是一個沉默的乞丐被當做了替罪羊之後,所有人的生活才重回正軌。那其實挺殘忍的,它完全顛覆了中年危機類電影的慣常路線,以一條狗的生命和一個底層人的自由為代價,幫主角重新找回了平衡。講世界墮入冰川期,僅存的人類被劃分等級放進一輛永不停息的列車。最終,居於車尾的底層人民發起反抗,向車頭進攻,是一個關於階級鬥爭的寓言故事。其中有個情節,打鬥過程中,起義領袖面臨一個選擇,是繼續向前衝,還是回頭救自己最忠誠的屬下。結果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向前衝,眼睜睜看著同胞被殺。同時,它也引起了一個思考:所謂起義領袖和那個坐在車頭的獨裁者,有什麼本質區別嗎?他們不過都是為了自己認定的某個“崇高”的理想,可以踐踏生命的人。說了這麼多,我其實是想說,《寄生蟲》對於奉俊昊來說,在價值觀上顯得太保守了。它用132分鐘的時間,描繪了一個過於淺顯、直白又無比正確的客觀存在。就像看一個叛逆的人突然變乖了一樣,哪怕那乖看起來挺順眼的,但心裡終歸覺得不舒服。到了《寄生蟲》的結尾,我們又見到宋康昊的凝視。不同的是,這一次,那把刀只停了片刻,便狠狠地刺了下去。
於是一切都走向確定無疑的答案,也留下了明晃晃的遺憾。
快給我好看!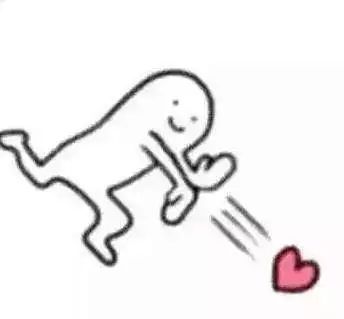


朋友會在“發現-看一看”看到你“在看”的內容